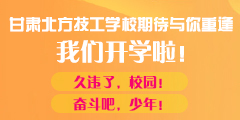唐润铧
一个高三学生完成了一部关于高三的纪录片。影片开始时,一张张苦闷的脸在重复着“所有人都一样”这句话,到了结尾,变成“所有人都不一样”。
上海市控江中学高三学生唐润铧在高中生涯的最后阶段,做起了导演、编剧、摄像和剪辑,一个人完成了纪录片《考在上海》。在这部24分钟的“电影”里,“演员”是他的同班同学,“剧情”就是整个高三生活。
镜头扫过夏日的操场,扫过红旗旁的教学楼,扫过课本和粉笔,最终定格在高三学生的面孔上。
背景音里的蝉鸣换成高音喇叭里励志的语言,橱窗里的海报换成各大名校显眼的校徽。高三前的动员大会上,刚刚考入大学的学长分享着高考的经验,台下400名穿着夏季校服的准高三学生或托着腮、或抱着肩、或歪着头,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。
画面有些抖动,唐润铧用“仰卧起坐到一半”的姿势,举着单反相机对着神态相差无几的那些脸,他既想将身后的大屏幕装进相框,又不想挡住后面的同学。在这场动员大会中,唐润铧在心里说,“该来的终于来了”。
对于二三线城市的学子而言,高考是一条艰难却极为有效的出路,人们对于高三的想象大多停留在拥挤的教室、垒得高高的课本、被精确计算到秒的时间上。
在这所能望见东方明珠的校园里,尽管高三并不那么令人窒息,所有人还是拼尽全力,包括已经申请了美国的大学的唐润铧。
他把高三的学生比作大海中的一粒沙,无力改变方向,只能祈求下一道浪能把自己抛得更远。
同学朱泽楠对此深有体会。这个爱笑的女孩认为,不用参加高考的“旁观者”唐润铧,比自己这个“当局者”看得更清楚。在高三第一学期的5次考试中,她为了提高7分,连续一个月每天刷两套试卷,“有一种不得不拼的惯性”。
身边的同学面对唐润铧的相机,一开始会躲闪。在习惯了他拿着相机“晃来晃去”之后,同学们终于把他当成了“一坨巨大的空气”。
为了拍摄教室的全景,唐润铧把课桌搬到了教室左前方的角落,当他举起相机时,没有一个人对他的镜头有反应。“高三,本来就没什么人抬头。”
镜头之外,白炽灯光照耀下的高三教室让人混淆了昼夜。唐润铧看到,有人在第一次月考之后默默地流泪;有人下课就跑去问老师问题。每个人都很自觉,整个教室的分贝比以前下降了许多。这种用功好像是存在于同学们基因里的东西,到了这个时候,“啪”一下就出来了。
对于要出国的唐润铧来说,努力的基因全部放在了托福和SAT(美国学术能力评估测试)上,他前后考了7次,每一次都像是高考。
1998年出生的唐润铧显出一种超越年龄的“老成”,“像是从过去穿越过来的”。他喜欢哲学多过足球,爱听崔健、许巍和朴树,向往上世纪80年代“文艺复兴”一般的自由氛围,愿意思考与分享观点。
他常年穿一件黑外套,书包和鞋子磨破了也毫不在意,留着“估计全区只有一个人梳的”油腻的三七分发型。在学校,有不认识的同学看到他,会毕恭毕敬地喊一声,“老师好”。
为了迎合美国学校的需求搞创新大赛、参加美国的夏令营拿外国人的推荐信、刷题考出高分的托福和SAT……在唐润铧看来,出国申请越来越成为和高考一样模式化的流程。
他曾感受过影片里溢出屏幕的紧张气息。那是在他备战SAT的时候,也是纪录片拍摄的关键时期。一场争夺时间的大战,在唐润铧和父母之间,一触即发。
“不是不让你拍,而是时间不对。”爸爸警告他,“如果因为拍纪录片而考得不好,你会后悔一辈子。”
唐润铧的犟脾气上来了,他认为高考有几个关键的时间点是必须要拍的,不能错过这个时间,他给自己的承诺是2015年底前必须拍完第一集。与此同时,他要一遍一遍往返于教室与留学机构的补习班之间,刚刚放下相机,又拿起了答题的笔。
“在高考面前,我总有点逃跑的感觉,一直没法抹去心里的罪恶感。”尽管与大多数同学走向不同的战场,唐润铧仍然希望为曾经朝夕相处的同学记录下这关键的一环,哪怕只是在旁边为他们竖起大拇指。
“我急啊!”妈妈陈霖是控江中学高三的语文老师,为了唐润铧的SAT成绩,焦虑得“快崩溃了”。他前两次的SAT成绩分别是1780和1990(满分2400),“你多做题总归多拿分咯,这是你最重要的事情!”
父母不支持他在备考期间拍片子,争执发展到最后,唐润铧表示:“我就要拍!我就要拍!”
在那间关了门的卧室里,他用了两个通宵,回放过去3个月拍摄的素材,154个G,1340个视频文件,然后埋头为片子写台本、录音、剪辑。
当第3次SAT成绩出来时,陈霖记得,唐润铧先是很平静地报了分数:2100,之后便“哇”一声哭了。
陈霖很心疼,觉得孩子在那段时间承受双重的压力。“作为一个语文老师,我很希望他有自由意志和独立思考的能力,但我也不能脱离对分数的追求。”
最终的SAT分数让一家人都挺满意,当被问到,“如果唐润铧没有考好还会让他继续拍片子吗”,陈霖斩钉截铁地说:“不会,绝对不会。”
唐润铧在上传自己的纪录片时,在网上留下一段话:我们从出生那一刻,就成了教育体制内的孩子,我们不得不面对当今中国不够合理的教育。一面针砭时弊的同时,我们又随波逐流。然而,我们真的别无选择吗?
一进入高三2班,首先会被教室后面的黑板报吸引,大面积黄色和蓝色的水彩颜料占据画面,田野和蓝天的界限从中间上下分割开来,一条棕色的、窄窄的小径延伸到远方,“高三之路”四个大字写在一旁,下面是一行小字:没有比脚更长的路,没有比人更高的山。
“从未来回想今天的时候,可能首先想到的是这幅画,而不是高三的重压。”在纪录片的下半部分,唐润铧讲述了老师和同学在高考的压力下,仍然保持自己爱好的故事。
拍摄的最后一个画面是圣诞节的班会,一串铃铛挂在黑板旁,老师和学生一起做起了游戏。旁白说,只愿这难能可贵的笑容能够一直留住,留到高考之后,留到成人之后。
镜头转向了高三语文组老师的办公室。在隔间的外墙上,贴着不起眼的三个篆体字——“后花园”。里面是一位语文老师的照片墙,贴满了苏珊·桑塔格、汉娜·阿伦特、卡夫卡、格丽泰·嘉宝的照片。这位老师自称有“空墙恐惧症”,不管办公室搬到哪里,她都不会落下这些偶像。
“很多老师有自己坚守的东西,即便被大环境吹得东奔西跑,也会坚守着。”这在唐润铧看来是一种反抗。
镜头里出现最多的,是一个坚持了25年的公益人文讲坛的发起者樊阳。
樊阳曾回到陕西的母校讲座,谈起对应试教育的厌恶。“我希望我的母校不要成为衡水中学。”台下的老师哄堂大笑,因为校长刚刚说过,要向衡水中学学习。
樊阳觉得,当唐润铧在考试面前,拿出时间拍摄这部片子时,应试教育的柏林墙已经在他身后倒塌了。
在老师眼里,唐润铧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“好学生”,甚至一度成为“老师最讨厌的那种孩子”。
唐润铧喜欢写作、拍片子,是合唱团团长,拍微电影拿过全国二等奖。文科成绩能成为年级前十名,理科成绩则是倒数十名。他向往美国更自由的校园环境,即便认为SAT很应试,但他知道这不是美国学校挑选学生的唯一标准。
当鼠标滑过各具特色的美国大学主页时,唐润铧才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是在挑选未来。他选择学校的原则很简单,一是看有没有哲学专业,二是希望在农村,他想体验不同于大城市上海的生活。
这个从小喜欢昆虫、为蟑螂写诗、会躺在花园里看星星的人,最讨厌的两句话是“长大了就懂了”和“社会会教你的”,他不希望长大,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把长大当作资本,而不是损失。
“我觉得高考是一场再合理不过的比赛了,规则很简单,只有那些在高考后保持住笑容和童心的人,才是赢家。”这是纪录片的最后一句话。
一个同级的同学说,对唐润铧的定义不要落在“是个有空闲时间的出国党”上,而是“本可一走了之却频频回头审视当下体制的学子”。
一位从教49年的特级教师说,一个面临高考的高中生,对于教育的弊端是最有发言权的。可惜,几乎所有的受害者都没有勇气或无力思考这个问题,他们只能在题海中苦苦挣扎。“有这样的学生,比出几个状元更体面。这说明,在今天的教育体制下,还是有空间的。”
唐润铧不喜欢用微信,他的朋友圈里只有每天背了多少单词的打卡记录。他觉得微信的表达廉价而容易,宁可选择短信,字斟句酌地谨慎表达。
唯一一个与年龄相称的爱好是玩电脑游戏。他不爱网游,喜欢一个人打单机游戏。最爱的那款叫做《黑暗之魂》。游戏的开始一片空白,玩家是个战战兢兢的普通人,一遍遍遇到强大的人,一遍遍经历死亡,最终成为英雄。当打到最后一关时,舒缓的钢琴曲响起,玩家又回归了混沌之初,他似乎战胜了什么,又似乎什么都没有。
每到这个时候,唐润铧都是一边哭一边按下回车键。
延伸阅读:
- ·高三女生和博导妈合发论文 恰满足自主招生条件(2015-06-04)
- ·高考季重温习近平勉励高三学子的真情话语(2015-06-05)
- ·高考季重温习近平勉励高三学子的真情话语(2015-06-05)
- ·高三老师道别:感谢同学们忍受我3年(2015-06-06)
- ·全面了解整个“高三”做到知己知彼(2015-07-26)

 护理专业
护理专业  多媒体制作
多媒体制作  铁路工程测量
铁路工程测量  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
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  铁道类专业专题
铁道类专业专题  幼儿教育专业
幼儿教育专业